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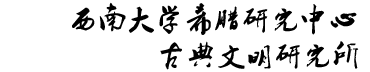
| 关于西方古史研究之历程的中文著作 张治 |
| (发布日期: 2017-06-12 10:59:17 阅读:次) |
《古典学评论》第2辑 关于西方古史研究之历程的中文著作
张治
这些年来,出现了几种以译介西方古典研究为主旨的丛书,比如华夏出版社与华东师大出版社的“经典与解释”丛书,上海三联书店的“古典学译丛”、“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广西师大出版社的“西方文明溯源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等等。整体看来,选题丰富多样而各有特色。但因为翻译工作未受到充分重视,也因为译者的能力所限,难免出现一些明显属于硬伤的翻译错误,有的甚至损害读者对原著的认知。学术翻译颇能考验专业学者的功力,长于学而拙于言者若肯贡献点儿力量,已经是不错的了,更多的问题却是与专业无关,都是大家熟悉的那些问题,包括稿费、考核体系云云,使行内人士觉得辛劳而无益。 北京大学自成立西方古典学中心以来,也在2013年夏天于该校出版社谋划了一套“西方古典学研究”的丛书。他们的策略看起来更为沉稳扎实,在翻译计划上似乎并不着眼于长久以来特别著名的经典,而是时下较为新出的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为读者着想很多,打算在资料提供上满足可靠性和基础性的要求,于是选择影印有些篇幅浩大的工具书与资料汇编。而另一方面,他们还优先选择出版了几部国内学者的重要著作,突出了“研究”的份量。 以我个人浅见,从这套丛书之著作部分的选题来看,当然是晏绍祥先生这部《古典历史研究史》最为重要。曾经有段时间,他的《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1999年,华中师大出版社)是不多见的指示西方古典历史研究历程的中文著作,我曾将之与谢德风先生翻译汤普森的四册《历史著作史》并观,是最初了解西方古典研究(偏重于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现在北大版的这部书相当于修订本,变动的面目很大,不仅篇幅上扩充为两大册,而且论述的章节也多有更换,体现出作者在更宽阔的学术视野下对原本论题的重新反思,也反映出进入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后一名严肃学者掌握“学术之公器”所展示出的自由程度。 《研究史》的上册与汤普森所论相比,于时代范围上多有重复。但是著作史与研究史,在命题上有所不同。研究史关注的范围可以更广一些,而著作史的优点则在于不拘于学术的对象,可以统观历代学人的成果(谢德风先生在译序中批评汤普森未能在观点方法的史学史角度上用力,故而《历史著作史》只算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史料学与历史目录学史)。研究史类似于某个学科史,其优点在于集中笔墨梳理各家相关研究的脉络,但若是学术通人奇才,往往不拘于既有学科的限制,从学科史的角度,未免关照起来有些狭隘,这可能是我们需要参对不同著述体例的一个重要原因。晏先生在序言中提到这部“修订版”有一重要的修改方案,与他近年的体会有关,即加重了文艺复兴至18世纪间西方古史研究领域的分量,因为他认识到“西方古史研究能够达到今天的繁荣和深入,绝非一日之功”。这个认识的“姗姗来迟”,与学术著作传统下学术史回顾鲜少上溯到18世纪以前的简略做法有关(这是就西学研究而言,关键在于彼方传统不曾中断,19世纪以来的学术大体可以全部覆盖此前的成果),但也是因为我们在认知西学传统上还很粗疏。影响作者的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对中国学界的意义比《历史著作史》广远重大,也想必就是这个原因。但即便如此,在此书中,文艺复兴到18世纪结束的篇幅,仍然不过73页,仅占全书的十分之一。很多介绍只能是走马观花,因此也就很难凸显出什么问题来。作者树立了史学研究的框架,因此把历史研究当成一个重点题目,而对于文艺复兴以来最为重要的话题之一,却是语文学角度上重新恢复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研究,在这个书题主旨的框架下,也就只能写成是一种文献学的努力,这有些扭曲和掩盖了当时学习古代语言时主要的文学目的,从而也很难发现17世纪以后所谓“新人文主义运动”者真正摒弃拉丁文作为学术著作主要语体的革命意义。另外,作者在文艺复兴时期一章中列有“博物学的兴起”一节,理应在论述17-18世纪的一章中跟进介绍博物学促成的古物研究和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的兴起,像18世纪法国古物学研究便是该国古典学术的最重要成就之一,但是这个环节至少在章节结构和主要论述上未能充分展现出来。及论及20世纪上半期时方再有“考古学”一节,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此间都无发展,不免有些可惜。 这部修订版的下册,专论20世纪下半期至今的西方古史研究,对于中文世界极有新意。作者提到的研究范围和研究著作非常广泛,以400多页篇幅列述出来,有种眼花缭乱的感觉。作者这些年多次赴欧美进修,网罗文献,采访学人,对20世纪下半期问世的大部头专著都有长久浸淫的阅读心得,才使得这部下册不仅满足于开书单,而是对很多要籍都有细节上的讨论。比如在介绍21世纪古史研究的著作时,作者对布莱克维尔公司的古代史指南所出各册逐一评述,又有总体上非常深入的思考。对于浅尝辄止的读者或是初次入门的学者,这些介绍和讨论势必会有很大的益处。但是“较真”一下,作者对新世纪所出版的学术著作和当代西方古史研究的新趋势描述,显然还是有些粗略,如果阅读一下刘津瑜女士《罗马史研究入门》,对比一下这部分的相关内容,便可看出想要梳理出更为全面和丰富的脉络,仍是中文学界一件颇为艰巨的任务。 即便如此,晏绍祥此书的伟大意义仍然不可动摇。他放弃了《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中西兼顾的尝试,不再列章节介绍中国的西方古史研究,这在此书的整体结构上是一个更为清醒的考虑。之所以如此,当然是中国的西方古史研究,或者古典学研究,还没起步。相比东邻日本而言,这是极令人抱憾的事。民国以来,中国人对于西方古典学术传统渐渐发生认知兴趣。胡适、陈寅恪以及李约瑟等人都曾强调中国学界应该系统了解西方古典学术史,与一般学者服膺某个时下流行的学派,或是藉由偶然性的条件对某些部分的古典研究发生兴趣不同,这样的识见自然更为超卓。古典历史研究史,并不等同于古典学术的历史。前者是对该时期历史研究的学术史综述,而后者的核心则是对该时期古典著作的研究史。晏先生的论述范围,实际上以史学研究为中心,略微旁涉与历史研究相关的学科,如考古学、铭文学、纸草学等方面,但如果是古典学术史,则应该以语文学的基础训练为根本。可是在近数十年间,西方古典语文学并无特别显赫的成就,而在各门新学科上进步更大。在西方古典学术的历史上,从语言文字的研究到一部部古籍的反复校勘编订,再到对经典文本的学术性翻译和考证性详注,这些工作在过去欧洲各国历代学人都曾经是有人倾其一生勉力为之的。我们渴望了解一个伟大坚固的学术与精神传统,当然就具有了从自身出发的怀抱和志趣。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再勉为其难地考虑中国在这个伟大传统中地位如何,未尝不是一个前进的起点。
|
 首页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