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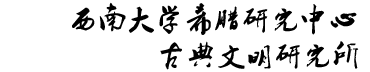
| 经济学家眼中的古希腊史——厉以宁《古希腊经济史》读后 |
| (发布日期: 2017-06-12 11:01:27 阅读:次) |
经济学家眼中的古希腊史 -——厉以宁《古希腊经济史》读后 刘峰
经济史是当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投身到经济史的创作之中,并产生了大量著述,厉以宁先生的《古希腊经济史》就是其中之一。本书由厉以宁先生的读书笔记、讲义和手稿整理而来,是其西方经济史系列著作中的一部分。笔者拟就上编中涉及的几个问题略述己见,以求教于各位专家读者。 一、关于荷马时代的社会与城邦制度的形成 厉以宁认为在荷马史诗时代阿卡亚人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阶段,实行的是军事民主制,[1]土地归部落所有,并由部落下面的氏族使用。[2]荷马史诗时代是否存在城邦,国内外学者意见未及一致。厉以宁先生认识到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摩尔根的观点在学界引发的诸多评论,[3]但并未就这些评论展开深入地分析,在后文论述仍然将氏族的存在作为荷马时代城邦制度并未形成的依据,认为荷马史诗时代结束后,城邦才在希腊形成。[4]在这里厉以宁将城邦与国家划上了等号,认为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也就是其国家形态的崛起。[5]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学术界关于国家的定义类目繁多,城邦的形成亦是万绪千端难以把握。国内外学者亦经常将城邦与国家混为一谈,诚然,城邦是国家初期的一种形态,但是二者决不等同,即使是古典时代较为成熟的城邦,也未必能够称得上是完备的国家。以往国内对于国家的定义国内一般遵从摩尔根-恩格斯的理论,认为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是:1、按照地区划分国民;2、公共权力的设立。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理论受到了较为强烈的冲击,许多学者认为地缘政治取代血缘关系并不构成国家形成的充要条件,自然也不能够成为国家产生的标志,以中国为例,夏商周三代主要是血缘关系社会。[6]近年来,以往少有争议的第二点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标志应该表明基本特征,具有识别作用,有学者认为公共权力设立的过程过于笼统,且时间跨度长,不适宜作为国家产生的标志。[7]国外对于国家的定义一般遵循韦伯所言,认为“国家是一种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成功地)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8]易建平在其文章中对此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评析,认为韦伯的定义仅仅能适用于现代国家,且武力合法使用权的限度难以把握,于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形成应该分为早期国家、成熟国家和韦伯定义适用的完备国家。《牛津古典辞书》中对希腊城邦特征定义为:“面积较小、政治自主、社会一致、具有集体意识、遵守法律。”[9]这样划分国家的发展过程有其合理性,笔者认为希腊城邦是早期国家的一种表现形态,但是这种早期形态的产生充其量意味着国家产生的条件已臻于完备,并不意味着成熟国家的产生,更不必说完备国家的产生了,因而城邦与国家并不能划上等号。 至于荷马社会是否存在城邦,厉以宁先生认为氏族社会与城邦之间存在一个部落联盟阶段,这个阶段不同于氏族社会,其基础并不是血缘关系,而城邦产生于部落联盟之后。[10]这时期的军事首领统称为巴昔琉斯,如果部落间发生争夺牧场、树林、水源等冲突时,部落全体男性成员都要参加战斗,部落首领就是统领,久而久之,大事的决策权就转移到军事统领手中。[11]希腊城邦作为一种早期国家形态并未脱离血缘关系,但不能因此就认定其并未发展至城邦阶段。厉以宁认为这一时期才产生的军事首领(即巴昔琉斯)的权利日益扩大成为后世国王。但实际上,巴昔琉斯这一官职在迈锡尼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其权力是日渐减弱的,巴昔琉斯在神谱当中被翻译成王,[12]认为宙斯是诸神之“王”。而后来在吕西亚斯将九执政官中的一名称为巴昔琉斯,且其仅仅掌管宗教事务以及各种秘密仪式。[13]且晏绍祥亦认为这一时期“将军的权利没有明显增长,也没有出现职业军队”[14],故不能将巴昔琉斯地位的变化作为区别氏族社会部落联盟与城邦的依据。上文有学者就国家的形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亦想从另外一个方面寻找城邦形成的标志,《牛津古典辞书》中的定义条理清晰详细,但就城邦而言最为重要的应该是公民集体意识的形成。集体意识的形成这一标志看似比较模糊难以把握,实则有迹可循,整体观念的发兴、公共领域的兴起、公众作用的提升都是集体意识形成的表现。厉以宁认为荷马时代的主要体制是贵族的oikos,即家庭,是一个个经济独立不与外界交流的单位,而不是一个享有治权的公民集体。但是这一观点似乎被荷马的记载所否定。《奥德赛》中佩涅洛佩首先问奥德修斯:“你是何人何部族?城邦父母在何方?”[15]奥德修斯其父也如此询问自己久未谋面的孩子。[16]可见当时人已经不拘泥于自我和家庭认同,于之上又有了一个更大范围内的认同,体现了整体观念的出现,只有在希腊范围之内有大大小小不同的集体,这样的问询才显得有意义。汉娜·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区分可追溯到城邦兴起之时,而且把公共领域定义为城邦领域,把私人领域定义为家庭领域。[17]可见城邦产生之时城邦与家庭已经有了区分,研究荷马时代的公共领域的情况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彼时社会状况。根据晏绍祥的研究,荷马时代公共领域已经有所发展,这是与私人领域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这个范畴之内的事务主要由普通人达成共识而决定。晏绍祥指出彼时伊大卡的精英被奥德修斯诛杀,本应由死者家属进行的复仇却被更多其他伊大卡人代替,这正是由于“普通人”基于对精英的丧失而达成的共识。[18]其次,公众的作用的增强是城邦产生的必要,希腊古代哲学家曾试图给城邦下过许多定义,都是基于人的作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例如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人是城邦的动物”,修昔底德说过:“组成城邦的是人,而不是那些没有人的城墙和舰船”[19]公众作用的增强体现在其在人民大会中的话语权以及宗教等方方面面。关于伊利亚特中特西提斯(Thersites)责骂阿伽门农这一材料,厉以宁认为这体现了军事民主制,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荷马社会在继承迈锡尼王权的前提下发展出的新政治组织。[20]但无论怎么解释,这都是下层公众在人民大会中话语权的体现。在荷马时代的宗教祭祀方面,权利也从原来可能由国王掌握,转到普通人的手里。[21]可见这几点在荷马社会中都有体现,故而笔者认为城邦的出现应比厉以宁先生所言更早一些。
二、关于希腊奴隶的几个问题 马克垚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指出厉以宁先生用供求关系分析希腊奴隶制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一大创新。厉以宁先生认为在城邦制度早期奴隶制和战争在希腊是相互依存的,奴隶制使战争成为必要,战争也是维持城邦内部稳定的必要,且希腊城邦与城邦之间发生战争是正常现象,和平共处则是不正常的。[22]在雅典改革和发展一章中,厉以宁指出,随着雅典城邦的建立,雅典经济得到了发展,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争。其后债务法颁布,许多自由民沦为奴隶,但是后者的规模远远不及前者。[23] 首先,关于战争是否是希腊城邦制度早期的常态问题。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左右,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间里,西方学界开始反思古代世界的战争,因而关于古希腊战争的论著逐渐增多。厉以宁先生认为古代此起彼伏的战争是希腊城邦制度早期的常态,以上结论主要参考了上述时间段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值得重新审视。厉以宁先生所说的希腊城邦制度早期大抵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古风时期,哈德蒙认为这一时期的战争目的有两点:一是争夺两国之间所属权有争议的土地;二是争夺霸权。并未涉及为争夺奴隶而发动的战争。[24]且以伯罗奔尼撒半岛为例,除斯巴达、阿哥斯经常参与战争之外,科林斯、麦加拉、厄利斯、特洛真等大多数城邦很少卷入对外冲突,因而能够享受较长时间和平生活。[25]厉以宁认为,战争能够缓和社会矛盾,减少贫富冲突引起的损失,这也是其坚持希腊战争频仍的依据,但是就整体而言贸然发动战争的损失可能更大,在战争结束之前谁也不能预知胜负,那么这场风险极大的冒险也有可能造成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厉以宁先生认为由于统计口径和时代差异等原因,很难得到雅典奴隶人数的具体数值,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希波战争第二阶段结束后,雅典的奴隶人数日益增多,而且进入公元前4世纪后增加得更多。[26]关于雅典奴隶人数的问题国内外学者著述颇多,但却未能得到一个全方位被认可的答案,此处暂不去论。笔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奴隶人数持续增长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厉以宁先生认为在雅典奴隶的使用是越来越多的,其依据主要是:一、奴隶使用成本低,使用奴隶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事情;二、奴隶主在订立奴隶契约时权利无限而责任却有限。[27]奴隶主必须要为努力提供其工作的工具以及喂养奴隶使其有能力劳作,豢养奴隶是否有利可图需要参看不同的社会背景与公民群体,雅典是一个小农社会,其能够容纳的奴隶数量是有限的,在奴隶数量达到饱和之时肯定不能断定仍然有利可图。根据铭文资料可知,养活一名奴隶每年至少需要225德拉克玛,与国家分配给一青年公民的口粮(240德拉克玛)相差无几,对雅典中下层公民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28]可见公元前4世纪雅典奴隶数量是否持续增长仍然需要结合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雅典社会情况来分析。关于第二点的有限责任,可以理解为雅典城邦经济发达之时,城邦承担雅典奴隶起义逃亡的风险,故而养奴隶风险很低。这样以来,厉以宁的结论便是建立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实力持续增长的基础之上,认为这一时期国家承担风险的能力是不断上升的。但是结合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时期雅典帝国分崩离析,雇佣兵兴起,信仰崩塌,虽然雅典经济有过恢复,但始终不能与黄金时代相提并论,这可能导致了雅典奴隶制曲折迂回发展,但绝不是本书中提到的持续发展。
三、希腊城邦危机产生的原因 厉以宁先生将希腊城邦危机分为两部分,一是城邦制度的危机,二是社会危机。实际上这样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细化城邦危机的表现,但是二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完全剥离开来,故而在此笔者仍然将其定为城邦危机。城邦危机是希腊城邦全面危机的总称,通过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军事危机、思想意识危机等不同层面表现出来,而经济危机则是根源。[29]本书对于城邦危机产生的原因论述较为充分,但是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并未体现,且厉以宁先生并未对城邦出现危机的时间进行界定,尽用较为模糊的如“后来”“之后”等表示时间。笔者认为,城邦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奴隶制的发展,前文已说到希腊城邦以小土地所有者为主,城邦所能够容纳的公民是有限的,而城邦危机的表现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就应该已经出现了。在公元前451年雅典政府规定只有父母双亲均为雅典人的才能够享有公民权利,[30]这表明公元前五世纪中期,雅典的公民数量已经达到了一定意义上的饱和,这也是奴隶制冲击下雅典小土地私有者开始分化的重要表现。雅典城邦危机的出现是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海外殖民掠夺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危机的加深,但是不能杜绝危机。其后,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冲击,投机商人肆起,政府已经不能够控制,甚至还要向投机商人妥协,已然达不到维护城邦制度的作用。
古代世界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表现出与现代社会的共同性,其资料也并未被全面精确地记录下来,这对于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阻力。许多问题亟待回答,但是答案却含混不清,就连最为细微的局部答案有时我们尚不能作出全面解答。我国对于古希腊历史的研究起步较晚,面对一个时间空间都相聚甚远的文明,至今为止我国学者所著大多只聚焦于某一方面,因而未有一部完整的全面论述古希腊历史的著作。《古希腊经济史》实际上是以经济为切入点带出了厉以宁先生对整个希腊古代社会经济的整体叙述。随着交叉学科的发展,我们能够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论进行古希腊史研究,但是现代经济理论是否能够使用于古代史的研究始终是有争议的。厉以宁先生作为一个当代知名的经济学家,其独特的经济视角仍然能为古希腊历史的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解读方式。
[1] 厉以宁:《希腊古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第48页。以下注释凡只用页码者,皆引自此书。 [2] 第50页。 [3] 第48页。 [4] 第60页。 [5] 第170页。 [6] 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3页。 [7] 易建平:《关于国家定义的重新认识》,《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8] 易建平:《关于国家定义的重新认识》,《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9] 参阅S. 霍恩布鲁尔等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牛津大学2012年修订版,第1170页。 [10] 第60页。 [11] 第51页。 [12] Hesiod,theogony .886.以下古典文献注释凡未注明者,皆引自Loeb classical library. [13] Lysias,against andocides :for impiety.4. [14] 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第95页。 [15] Odyssey.19.105. [16] Odyssey.24.298. [17] 黄洋:《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第82页。 [18] 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第106页。 [19] 修昔底德著;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28页。 [20] 黄洋:《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1页。 [21] 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第107页。 [22] 第77页。 [23] 第187页。 [24] 晏绍祥:《古风时代希腊陆上战争的若干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25] 晏绍祥:《古风时代希腊陆上战争的若干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26] 第361页。 [27] 第362页。 [28] 徐松岩:《关于雅典奴隶制状况的两个问题》,《世界历史》,1993年第5期。 [29] 郭小凌:《希腊军制变革与城邦危机》,《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 [30]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VI. 3。 |
 首页
首页